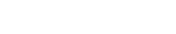哈佛醫給失智妻的情書「我成了她的引路人」
知道診斷結果那一晚,瓊安想到我們所害怕的狀況已近在眼前而痛哭悲傷不已,我把她緊緊抱在懷裡,強烈表明我會為她竭盡所能的決心。她憤恨地悲嘆我們就要展開的黃金歲月,為此我們已經做了那麼多準備,然而一切即將截然變色。我承諾,無論發生什麼事,我都會好好照顧她,而且她會永遠留在家接受照料。她不同意我這樣做。事情不是這麼簡單。最後,就在我們睡著之前,她用雙手捧住我的臉轉向她,直視我的雙眼。我可以從她臉龐看出來她理智清晰、清醒,而且下定了決心。她以慎重的語調堅定地說了一段話,這些話我從來不需費力去牢牢記住,因為這些年來她一直以同樣嚴肅的認真態度重複這些話。它們永遠地烙印在我的靈魂當中。
「我不想苟延殘喘。我不想死得沒有尊嚴。你和查理(初級照護醫師)會明白什麼時候該讓這一切結束。你必須答應我。我需要你的承諾。」
我聽著。我表示出我聽見她的要求了,但是即使在那時我就知道,我和她的醫生們實際上能做的並不多。我和她一起哭。為她而哭。為我們而哭。但是我不知如何是好。不, 我深深地心知肚明,無論我們遭遇到什麼,無論她要求我什麼,我絕對無法奪走她的生命。我們要一起(我心裡這麼想著,但是沒辦法大聲說出來)承受這一切,即使那是無法承受的苦厄。
阿茲海默症很少會依循任何常見的故事發展模式來進行。它確然會有開端,也無可避免地會有結束,但中間的部分──以照護為重心的漫長奮戰──對於大多數的病患和家屬而言,是一團說不清楚而且經常難以理解的混亂。許多不同的阿茲海默症專家和權威,往往將這種疾病描寫成好像它會按照界線分明的階段逐一進展。我很清楚,這樣的劃分方式可以讓處理和討論疾病容易些,但是我們在疾病中生活的經驗卻完全不是如此。我們自身的病痛故事根本不是線性進行的;它毫無章法而且不可預測,有時候甚至完全任意變化。故事經常倒帶重來一次,實際上充滿著上軌道然後又重新來過的狀態;學習到一件事,然後忘記,之後又再重學一遍;悲喜交加的經驗一再一再地重複,就像一首主題與變奏沒有獲得解決的組曲。
在這十年的過程中,生活對我們來說確實幾乎令人熬不下去,不過瓊安一開始並沒有視力以外的症狀。慢慢地,經過好幾年的時間,瓊安枕葉的神經突觸繼續萎縮,讓她完全失明。某種程度上她拒絕承認,她非常努力掩飾自己失去視力的程度,以及隨之而失能的結果。但是瓊安在生命的末段才失去視力,已經沒有時間學習其他生活方式作為補償。漸漸衰敗的眼盲表示她無法再繼續翻譯或閱讀《千字文》這篇儒家傳統用來教育孩童、在歷史上十分重要的韻文,她已經致力於這項工作有十年之久了。
瓊安不只在學術工作上遭受打擊,更因為她無法使用電腦、閱讀我們的研究資料或是與親友通訊,而讓情況雪上加霜。隨著時間進展,她再也不能看電影、逛她心愛的博物館或畫廊,或是欣賞我們四十年來收藏的中國繪畫,而這是經常為她帶來喜悅的一項嗜好。我無助地看著,看著她一點、一點地失去構成她做為一個人的價值和感知的深層核心,看著造就她之所以為她的所有事物崩解消失。
隨著這些不斷進行的喪失,瓊安也不得不面對她漸漸無法獨立生活的狀態。起初, 她發現自己已經不能再依靠些微的視力獨自安全地過馬路,這表示如果沒人陪伴,她不能離開家裡或辦公室。到了後來,她沒辦法一個人自己在家裡走動。在我們去兒子家做客期間,她沒看見前面有一層樓梯因而摔了下去,把骨盆給摔裂了。那次可怕的墜樓經過漫長復原之後,她總是緊緊抓著我,即使是在我們自己家中。
因此,我成了她的引路人。我牽著她的手,吻著她的手和臉頰,一開始這是為了提醒她,她是多麼深深地被愛著,之後當她的認知功能惡化時,則是為了讓她知道牽著她的人確實是我而感到放心。我帶著她在我們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的家中到處走動;繞過椅子和桌子,經過沙發和書架,從臥房到廚房,從客廳到餐廳,從我那擺著電腦和電視的書房,到她那排列著書籍的書房,裡頭放滿中國文獻和字典、法文小說以及書法與中國繪畫書籍,在不久之前,她經常開心地臨摹這些書畫。在那間牆上掛著她自己繪畫的松樹和岩石的書房裡,她會畫出彩色的線條、漩渦和碎片,隨著她的記憶與理解力喪失的程度追上她視力喪失的程度,這些圖樣變得越來越鬆散、越來越抽象,直到她再也看不見任何東西。即使在她接近全盲的時候,畫畫依然能讓她冷靜下來,大多數的古典音樂也是如此。對我來說,最令人心碎的景象,是看著瓊安試圖掩飾自己視力喪失的程度,露出滿面笑容衝向親人和朋友想要抱住他們,卻全然朝向錯誤的方向。
本文授權心靈工坊出版《照護的靈魂:哈佛醫師寫給失智妻子的情書》
好東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 !!
趕快來加入我們優照護吧~^^*